“戏剧艺术以及戏剧理论研究,站在戏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不能一味地强调戏剧与文学不一样,而是要努力从文学以及更多的其他艺术门类中吸取滋养,从其他的文艺研究成果中,获得新思路,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研究方法。”

《静·安》杂志:
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期间,注重教学和科研的文学素养。《焦菊隐戏剧论文集》《曹禺论创作》《老舍论创作》《李健吾戏剧评论选》,王元化先生的《莎剧解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编选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易卜生评论集》、洪深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德国戏剧评论家莱辛的《汉堡剧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戏剧小工具篇》、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的《迈向质朴的戏剧》、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的《空的空间》、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法的《残酷戏剧》、焦菊隐翻译的俄罗斯戏剧家丹钦科的回忆录《文艺·戏剧·生活》、上戏教授余上沅翻译的美国戏剧家乔治·贝克的《戏剧技巧》、苏联戏剧家梅耶荷德的《梅耶荷德谈话录》等,都是您竭力推荐的书目,您还给导演系和戏剧学院的师生开设讲座《从小说到戏剧——从〈狂人日记〉〈尘埃落定〉〈长恨歌〉说起》《曹禺与李健吾》《论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朱光潜与20世纪中国戏剧批评》等,希望大家关注文学与戏剧的关系,将戏剧的文学基石打深打实。看来您是认同戏剧可以从文学中汲取养分的,而且认为文学是戏剧的重要基石?
答
我在高校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前后大概有30年了。从文学审美角度看世界,从文学史的视角思考审美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以文学审美为核心来吸收相关的艺术门类的知识以及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是我平时的日常功课。可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艺术兴趣是比较广的,从几十年来购买的书籍和艺术品中就可以看到,有关艺术方面相关的著作、图册、影视碟片和音乐唱片等,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断断续续,收集了一些,至今没有终止过。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我的知识储备,也构成了我的艺术认知谱系。从这些相关材料中,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艺兴趣所在和平时的喜好的。如果一定要问文学与哪些因素有关联的话,那么,我认为与文学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因素的组合方式不同,呈现的思想结果和特色也不一样。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华东师大读书时,徐中玉教授、施蛰存教授就一直讲,研究文学的人要做杂家,各种各样的书都要读。我博士生时期的导师钱谷融先生也一直教导我,书要看得杂一点,兴趣不妨多一点,对文艺作品要有感觉,这对研究文学是有好处的。——这与复旦中文系朱东润先生当年教导学生必须把一部书学通学精的专家治学方式,形成了对照。在这些杂多的文艺兴趣中,戏剧毫无疑问是我的兴趣所在。从1981年9月进华东师大中文系开始,10月就参加在上戏举行的上海市大学生歌咏比赛,我们还拿了一等奖。几十年下来,观摩过无数的戏剧。尤其是在上海展演的话剧,看得比较多。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毕业大戏,很多都看过。像曹禺的《家》《原野》以及莎士比亚的一些戏剧,都曾在上戏的实验剧场看过。还有像《绝对信号》《车站》《肮脏的手》《芸香》《太阳河》《护照》《WM》《李白》等,也在上海的一些剧场看过。记得1990年我读博士时,我的一位朋友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工作,他不太喜欢戏剧,但他的工作就是看戏,看完后还要写剧评。他见我喜欢看戏,就把票子给我,让我去看戏,看完戏后写剧评。我记得看黄梅戏时,观众基本上是一些老头老太,像我这样20多岁的年轻人真是很少。90年代的《上海艺术家》发表过我好几篇剧评。所以,对戏剧我是不完全陌生的,觉得观剧和看一些不同剧种的优秀剧作,对我思考文学问题是有帮助的。
但2018年到上海戏剧学院担任行政职务,分管学科和创作等,要与专业人士打交道,这跟原来的兴趣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立脚点要转到戏剧方面来,是从戏剧专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上海戏剧学院是中国戏剧艺术领域的最高学府,与中央戏剧学院一样,在海内外享有良好的声誉。那么,从戏剧角度来理解问题,该注重哪些呢?当然,人们会说,戏剧与文学是相互关联的,这没有问题,但也不是那么简单。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最好的作品,基本上都不是戏剧学院贡献的,像曹禺的《雷雨》和《家》,像老舍的《茶馆》以及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经典作品,其底色不是戏剧,而是文学。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讲曹禺、老舍、夏衍等,都是在文学史范围内来认识的,相比之下,今天去问一个中文系学生,是否能推荐一部最新的戏剧作品,估计很难,因为今天的戏剧,从戏剧角度讲是戏剧的戏剧,也就是一些人说的为戏剧演出而创作的文本,是演和看为主的戏剧,与原来可以阅读欣赏的文本本体时期的戏剧有所不同,今天有的戏剧导演是没有剧本的,只是导演讲一下对手戏主要情景,然后由演员去自由发挥。从戏剧本体考虑问题,很多戏剧人会强调戏剧与文学分离。所以,站在戏剧的角度看戏剧与文学的关系,与站在文学的角度看戏剧,理解上是有所区别的。
我参加第五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担任史料卷主编,看到一些材料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时,最初是上戏的吴仞之先生负责的,吴仞之教授是舞美灯光方面的专家,人民大会堂最初的灯光设计者之一。但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其他各分卷主编在一起,估计话不投机,吴仞之先生最后是称病退出了。估计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一细节,但我以为从这一事情上可以看到,新文学大系尽管也有戏剧、电影等分卷,但从根本上是立足文学的,而站在戏剧、电影角度,像吴仞之先生等可能会觉得应该尊重戏剧、电影等艺术的独特地位和专业特色,不能简单地比学问、比问题意识、比文史修养。如果这么一比,搞戏剧的,很多人是受不了的。连吴仞之先生这样的前辈当年都受不了,今天很多搞戏剧的大概就更不用说了。大家可以去看看汪曾祺在《晚翠文谈新编》中有一篇谈戏剧的文章,他主张戏剧与文学分家。他是熟悉中国传统戏曲的,很长时间都在北京京剧院做编剧。他觉得戏剧与文学要分家,我想这是他在这个行业中浸润时间比较长,有了一些体会,也有了一些认识。他强调戏剧与文学分家,但又强调戏剧要有文学的基础,单靠原有的这点戏剧积累,是行之不远的。

《静·安》杂志:
2023年8月,上海的表演艺术家奚美娟女士的散文集《独坐》出版,在思南文学公馆有过一个新书分享活动,您作为嘉宾出席并讲话。奚美娟是上戏毕业的学生,在舞台和银幕上成功塑造了无数角色,受到大家的喜爱,也引人关注。她的成功经验中有一条,就是除了表演实践之外,平时还得多看书学习,尤其是要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增强自己的阅读分析能力和感知能力;另外,最好还要自己能够动笔写一点东西。这种有文学意味的表演艺术追求,揭示了文学阅读之于戏剧的重要性。不知道您有什么具体的看法?
答
如果将文艺理论的研究著作与戏剧理论的研究论著相比,在今天的中国,肯定是文艺理论著作更为丰富,深度也要超过戏剧研究。所以,戏剧研究包括戏剧艺术很多方面是受到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思潮的影响、启发的,而不是相反。这反过来说明,戏剧艺术以及戏剧理论研究,站在戏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不能一味地强调戏剧与文学不一样,而是要努力从文学以及更多的其他艺术门类中吸取滋养,从其他的文艺研究成果中,获得新思路,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我看新中国戏剧领域最具影响的一些戏剧家,像焦菊隐、黄佐临等,文学修养都是极高的,他们不会像一般的艺人那样只会谈一点演艺经验和心得体会,而是能够将演艺经验上升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理论层面来思考和阐释。我今天读焦菊隐、黄佐临先生的文章,感触非常强烈,不仅是其中的道理说得透,而且问题也归纳到位,行文流畅,思路清晰。这与今天很多戏剧领域从业者的文章文风形成反差。我到上戏之后,一直与一些老师、学生学习交流,强调要看书写文章。记得复旦的朋友遇见我就笑话我,——演戏的你要他们看书写文章干什么?我就以焦菊隐、黄佐临的例子回答他们。当然他们也会说中国有几个焦菊隐、黄佐临?但我想每一个艺术行业都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人物,像焦菊隐、黄佐临就是中国戏剧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后来人应该追随他们的业绩,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剧团和普通的演员可能不一定看书写文章,但像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顶级艺术学院,培养演艺人才的地方,是应该提出这样的理想目标的。有些人把看书写作视作与戏剧教育、戏剧实践相对立的东西,认为书看多了,文章写多了,戏反而不会演了。我想这是不对的。戏剧教育不能弱化这方面内容,努力与不努力,强化与不强化,造就的戏剧人才的艺术格局是完全不同的。
2023年我看到濮存昕、奚美娟出版了他们谈戏剧表演方面的书《我与我的角色》和《独坐》,另外还有已故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先生的《李默然戏剧笔记》、于是之先生的《于是之全集》,还有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的《导演小人书》等。读了之后觉得有收益,这些表演艺术家不像一般的演员,没有演完戏一切就结束了,而是坐下来思考一下如何总结自己的表演经验,如何运用文字来将这些宝贵的表演体会整理出来,发表、出版,与更多的人交流、探讨。这对戏剧艺术来说,是一种比较高的追求。一种艺术门类在艺术上之所以能够抵达比较高的境界,与从业者的理想目标、努力程度和文化素养是有关的。通过读这些表演艺术家的文字,我深有感触。

《静·安》杂志:
您曾经撰文称赞静安戏剧谷带来的以色列卡梅尔剧团的《安魂曲》和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剧团演出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认为展示出对经典戏剧重新提炼的“新趋势和新高度”。您也肯定立陶宛导演斯图米纳斯的《三姊妹》,认为在戏剧语言上进行了重新编码,“对年轻的观众而言,有一种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近距离感”。对于这些观赏剧目以及对人们戏剧观念的影响等问题,您有些什么看法?
答
从事戏剧艺术的人,比较感性,重技艺和舞台实践,对一些抽象的理论方面的问题,普遍考虑得比较少,或者不感兴趣。但回顾我自己数十年来的研究、学习体会,我觉得文学艺术,包括戏剧艺术不应该也不能放弃抽象的思考,包括理论思考。文学领域,比较明显,那些重要的文学审美变革,背后都有抽象的理念支撑着,尤其是哲学观念和文化观念。所以,文学领域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读一点哲学书,甚至是一些搞创作的,都会将自己的创作与哲学关联起来。戏剧领域,我不太清楚有多少人关注那些观念形态的东西,但像焦菊隐和黄佐临等,他们当年是关注的。如果读过焦菊隐翻译的丹钦科的回忆录译后记的,一定会被焦菊隐的这种深刻的理论思考所深深打动。还有像黄佐临在60年代提出“写意戏剧”以及他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积极推荐,其背后的理论资源是他对西方现代戏剧理论的了解、掌握,以及他能够在舞台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思考。这都是新中国戏剧领域中最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没有观念的支撑,不会有北京人艺的《茶馆》,也不会有80年代一系列的戏剧实验。只是这些观念的东西是隐形的,不像舞台表演那么直观,以至于一些人误以为戏剧创新主要就是生活积累问题、舞台实践问题,一味主张到舞台上去锻炼,完全忽略了艺术抽象观念的影响及作用。新世纪以来,中国戏剧之所以没有出现像《雷雨》《家》《茶馆》这一类经典作品,根本原因是审美观念上没有新的拓展,也就是虚的这一观念层面没有建构好。所以,上戏前两年创办了集刊《戏剧评论》,一年一期,慢慢希望一年两期,甚至更多,着意于戏剧观念上有所建树。
我最近重读王元化先生的《思辨随笔》,其中有一篇是他1986年写的不赞成莎剧的昆曲改编的文章,可能是针对黄佐临先生推动的莎剧中国化,特别是用昆曲来演绎莎士比亚戏剧,以此探讨中国传统戏剧现代化。现在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化,很多都是沿着这一条路子走的,用中国传统戏曲的形式来演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其他外国的戏剧。但王元化先生从莎剧演艺传统和美学理论层面,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开始在中国演出,要严格采用道安废弃革义和鲁迅主张的译文保存洋气,而不能以外书比附内典(格义)及削鼻挖眼(归化)的办法”。他主要是围绕美学中的“真”的概念做文章,如果戏剧改编,原作的真味全失,还叫什么改编?就像一些人将古希腊的《俄狄浦斯》仅仅是取其故事,用一个杀父娶母的故事,以昆曲、秦腔的样式表演,美其名曰——中国戏曲的现代化,这样的戏剧探索模式,王元化先生是反对的。所以,他借莎剧的中国传统戏曲改编来说事儿,我觉得这一意见是值得戏剧从业人员思考的,不要一听到批评意见,就认为是否定自己。今天从事文艺研究的学者,很少有像王元化先生那样,对戏剧持有热情和关爱的,正因为爱之深,才有那样的批评;而戏剧领域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像黄佐临先生那样虚怀若谷,能够倾听各方不同意见。我们应该向前辈学习,破除杂念,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除了多看各种戏剧作品外,戏剧观念建设应该紧紧跟上。
《静·安》杂志:
静安戏剧谷是推进上海戏剧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您如何评价这项工作?
答
静安戏剧谷是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一张名片,它持续十多届了,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优秀剧目和国内其他地方的剧目,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可能最初举办戏剧节的初衷有经济上和其他因素的考量,但客观上,它是开阔了戏剧审美的眼界,像前面提到的以色列卡梅尔剧团带来的《安魂曲》、俄罗斯亚艺术家带来的《三姊妹》《钦差大臣》等,无论舞台呈现还是戏剧观念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我觉得大家还应该继续努力,尤其是应该学习世界上高水平的戏剧节的经验。2023年暑期,我去法国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三周时间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台剧目上演,其表演形式之多样,表现内容之丰富,表演手段之复杂,让人大开眼界。对比之下,我就在想,法国一个小镇都能够有这样的号召力,吸引全世界这样多的剧团来演出,而且大多数是自费的,我们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政府出面,其社会影响力和实际收效,应该超越现有的预期目标。我感到一方面在社会运作的方式、机制上,还应该有新的作为,不能所有的演出都由政府包揽、出资,而应该多发挥一些社会运作的力量;另一方面,在戏剧审美意识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强化,让戏剧节真正成为国际大都市不可或缺的艺术嘉年华,成为引领戏剧审美潮流的驱动力。
事实上,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我们看到那些在文化上没有标识度的城市,是不可能在其他方面大有作为的。上海的戏剧艺术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应该体现自己的作用和优势地位。静安戏剧谷先试先行,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应该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另外,上海国际艺术节也是一个代表上海城市文化水准的艺术节,包含了不少戏剧艺术的内容。这些艺术节除了应该不断扩大展演规模之外,目前还需要增加一个活动,这就是艺术观念引进、梳理、澄清和提炼的培植环节。培养和建构城市的戏剧审美文化,不能没有评论,不能没有观念的参与与建构。黄佐临先生当年排布莱希特的《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最初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和积极响应,原因之一,就是在戏剧观念上,人们不习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很多人以为看戏就是照原来习惯的套路看,演员也是习惯于原有的讲故事的套路演。黄佐临先生用“跳进跳出”的方式导演戏剧,不仅观众不习惯,演员也不习惯,但多少年坚持下来,人们最终还是习惯了这种戏剧。所以,单靠演艺本身是不能有效形成新的戏剧理论和戏剧观念的,总需要有观念方面的提炼和研讨,这样才有可能促进戏剧生态的良性发展。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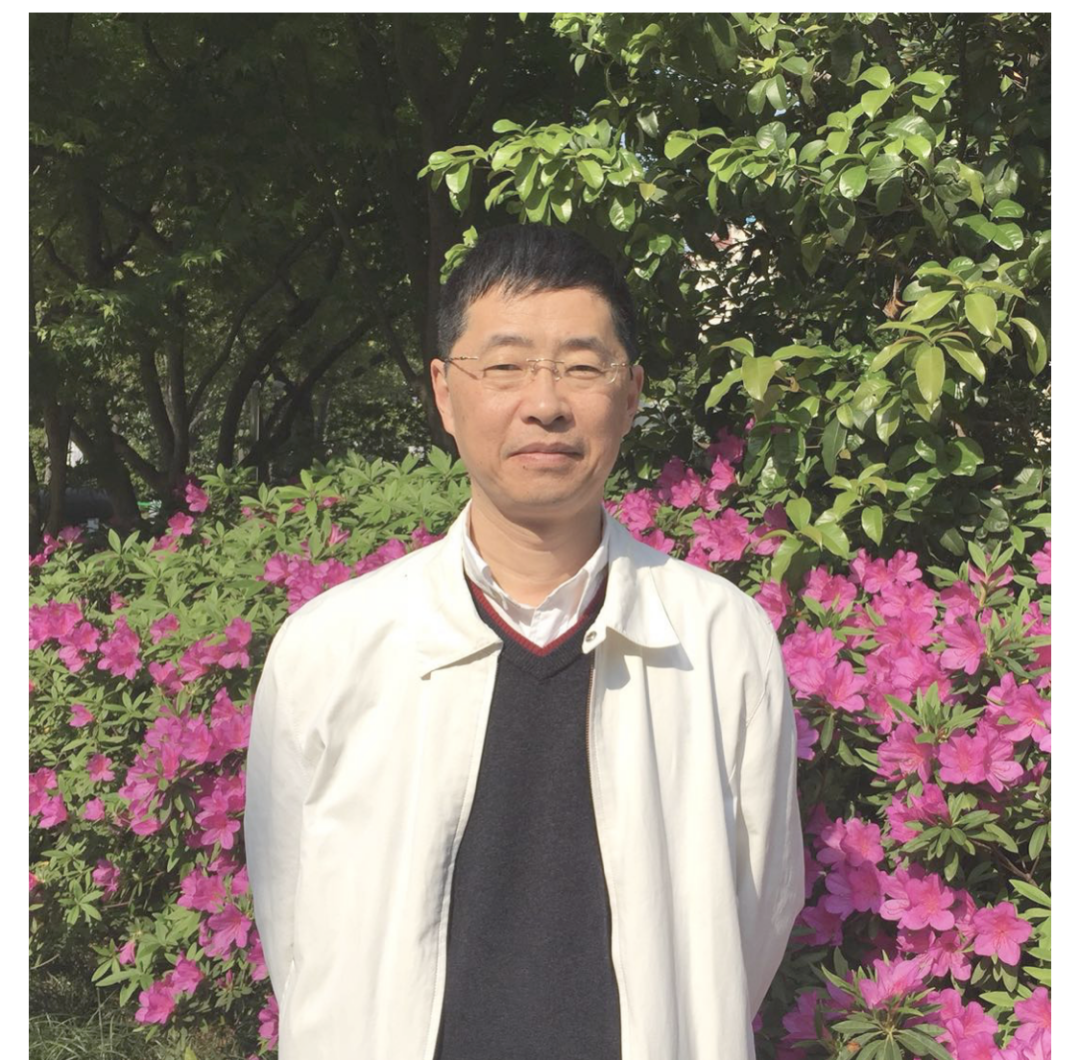
杨扬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中国田汉研究会副会长、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艺术》主编。曾担任《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主编、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第五至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第七至十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第三十一至三十三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评委会副主任、《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史料卷》主编。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文汇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发表上百篇学术论文和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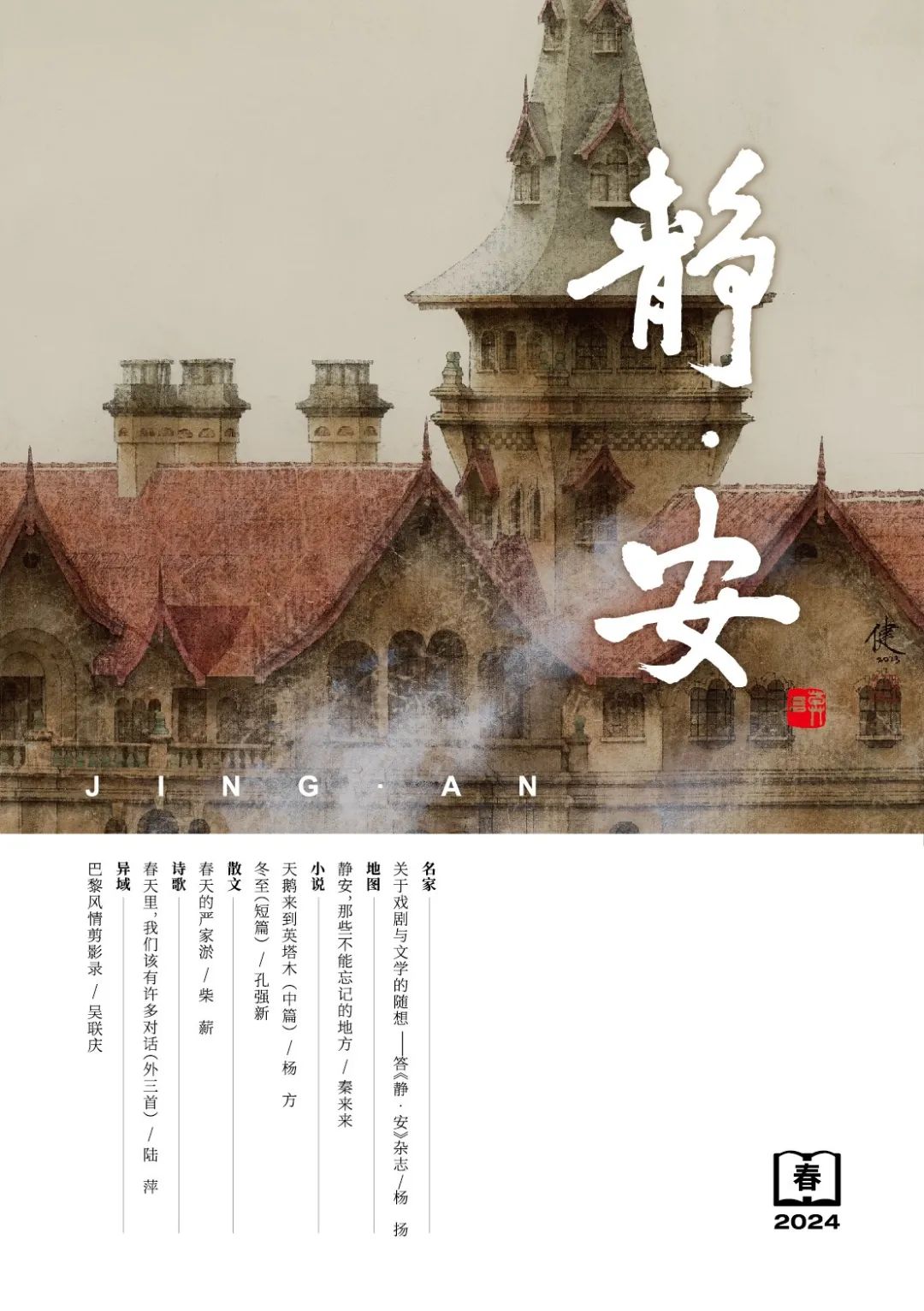


扫码关注我们
静安区作家协会
微信号|jaqzjxh
投稿邮箱jaqzjx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