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或许太小,小到连这些问题都没有好好想,好好问。但长大了又怎么样呢,我还是没记得问。又比如都说外公的毛笔字写得好,我却从没跟他好好学过。我只是越长越大,去外婆家的次
数越来越少。”

一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这是我记得为数不多的童谣,也仅仅记得这两句,却像是长在了心坎上。
我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什么都好,就是孤独寂寞了些。在我还是个小孩子、渴望有人陪伴的时候,却常常独自在家。所以,我喜欢去外婆家。外婆家有外婆、外公、舅舅、阿姨和表妹,人一多,做什么都带劲。
外婆是个顶能干的人。你要问有多能干,反正我觉得这一大家子全靠她撑起来。虽然我妈说外公才是顶梁柱,但我看他总拿张报纸一坐半天,啥活儿都不干。外婆可是忙里忙外,除了在上外学生食堂上班,还要负责家里的一日三餐、清洁打扫,家务活全包全揽。
外婆烧得一手好菜,一碗肉饼子炖蛋,光倒点汤我就能干掉三碗饭。每天她一早去菜场买菜,准备早饭,大饼、油条、泡饭、腐乳、酱菜、咸蛋,品种齐全,再给我下碗小馄饨,那味道真是谁也弄不出来。晚饭不烧菜的时候,外婆就包大馄饨。桌子上只摆一锅酱油汤,每人舀几勺到盛了馄饨的白瓷碗,你一碗,我一碗,围在一起吃得稀里呼噜。人多热闹,胃口便好,我那时的最高纪录是一口气吃了二十一个馄饨,撑到不得不去松裤腰带。
过春节,外婆更是忙碌。蛋饺、肉圆、汤团的制作,全由她亲力亲为。而我正放寒假,可以在外婆家开心自由地多住几天。外婆做蛋饺,我蹲在一旁看,忍不住也要弄两个试试。长柄圆勺在火上烧热,夹一块肥猪肉滋啦滋啦地擦拭,倒一调羹蛋液,转啊转转啊转,转成圆圆的一片,加上肉末,再用筷子把两边的蛋皮粘起来,油亮金黄,香气扑鼻。
做肉圆,我基本是等着吃。外婆把炸好的肉圆从铁锅中捞出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放一个进嘴里,烫得直哈气。说实话,什么红烧,什么放汤,刚炸好的才原汁原味,热热乎乎,吃得人心满意足。
做汤团工序有些繁复。首先要去整个石磨来,这家伙重得不行。磨嘴上套个布袋,然后把洗好的糯米一勺勺放进磨盘上的口子里。外婆叫我放糯米,我却喜欢转磨盘,看乳白色的汁液从两爿磨石的缝隙里不停地流出来。但这活儿其实不好干,转几下好玩,转多了就没力气,于是交由外婆全权接管。外婆放一勺糯米,转几圈磨盘,转几圈磨盘,放一勺糯米,周而复始。等糯米放完,布袋里的汁液已满满当当(奇怪,居然不会漏),取下来扎紧袋口,平放在地,压上重物,过一个晚上,里面的糯米汁便结成了糯米粉。哦,这还只是第一步。
吃年夜饭,人多菜多要摆圆台面。有时去云南插队的大阿姨和宁波的表姨会带着小表妹、小表弟来,挤不上圆台面,外婆就把我们几个小孩安排在一旁的小桌。虽然上不了主桌,好吃的却一样不少,且往往能先吃为快。切好的红肠和酱牛肉、拌好的海蜇和萝卜丝、炸好的春卷和龙虾片、炒好的虾仁和鱿鱼块,外婆总是先盛一点到我们这儿,汽水也有得喝,小杯子碰一碰,不要太开心。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们还在睡梦中,外婆已经搓好了一个个滚圆白净的黑洋酥汤团,用半湿的纱布盖着,起来每人吃一碗,团团圆圆。还有奶油蛋糕,奶白、麦淇淋、纯奶油,白色、咖啡色、奶黄色,一种比一种上档次,装在高高圆圆的纸盒里,多半是亲戚朋友拜年所送,切开来一人分一块,甜甜蜜蜜。我大抵总能吃到一朵花,舅舅、阿姨可以吃到一点绿叶或“新年快乐”,外婆则总省给我们,自己连边边角角都不吃。
天气慢慢热起来,外婆开始腌咸蛋。鸭蛋抹了黄泥巴封进缸子,到时候拿出来洗干净,煮熟了就能过泡饭。立夏那天,我还能用红色的网兜装一个挂在脖子上显摆。
端午,外婆会包粽子。鲜肉粽、白米粽、赤豆粽,口味丰富。我最爱吃鲜肉粽。洗干净的碧绿粽叶圈起来,放进白花花的糯米,加一大块五花肉,粽叶折几下,绳子绕几圈,扎成个紧实的三角包。这活儿以我的动手能力,则完全插不上手。
夏天的夜晚大家围着吃西瓜。西瓜捧出来往桌上一放,外婆手起刀落,脆生生切好几排,你一片,我一块,须臾便被消灭完。买西瓜的任务多半由舅舅负责。白天他顶着日头溜达出去,不一会儿就扛回一麻袋西瓜,搁到床底下,每晚挑一个出来吃。

二
我读小学的时候,舅舅因为单位远周末才回来,每次回来就接上我去外婆家。舅舅待我好得没话说。比如,若我对什么吃的玩的有点想法,只要站在摊头或柜台前多望两眼,他就立马要掏钱了。不像我妈和我阿姨,带着我和表妹逛街,我俩看中一个玩具,跟在她们身后哭了一路也没给买。
每次我赖在外婆家不想回家,舅舅总是帮我说话,他接我去外婆家的次数也最多。有一次里根访问上海,公交车停开,车站上挤满了人,天快黑了还是一辆车子不来,我都记不得那天是怎么到外婆家的。又有一次舅舅来接我,拎着个褐色的缸子,里面一整块不知道是海蜇还是水母的东西(这俩是不是一种东西),泡在闻起来酸酸的水中。那缸子沉得不行,再加上大半缸子的液体和那一层厚实之物,一路上晃晃悠悠,真是艰难。舅舅把缸子放在地上休息,我跑过去帮他拎,根本提不起来。不知道他哪里弄来,也不知道吃了有啥用,总之是孝敬外婆的。嗯,舅舅一直是个孝顺的孩子,是外婆大大的福气。
大阿姨从云南回来会带好多东西,多到扛不动。我最喜欢她带的油鸡枞,就是汪曾祺散文里写的那种,但我觉得比散文里写的还要好吃。她在山里挑了野生的鸡枞菌回来,用辣椒和油炒熟了装进罐子,一路带到上海。云南的菌子本就有名,汪曾祺说鸡枞是菌中之王,味道鲜浓,无可方比。你想想,把如此之物加了辣椒在油里煸煸炒炒煎煎熬熬,精华尽出,那是怎样的味美啊!单说下面条,往汤里添一撮,其他什么都别放,味道就好上天。便是只滴几滴熬鸡枞的油,也要鲜掉眉毛。
大阿姨还会做煎饺(这个只有她做得好),她回来我们才吃得到。冬天周日的傍晚,妈妈领着我从她厂子里出来。天气阴沉沉,又暗又冷,我立在公交站头,想着明天一早又要读书,心里简直凄风苦雨。妈妈说我们去外婆家吃晚饭吧,我一下惊喜。到了外婆家,大阿姨正在做煎饺,又是大惊喜。虽然晚上还要顶着寒风回去,但感觉真是赚到了呀。
三阿姨又叫上班阿姨,小阿姨也叫读书阿姨,因为那时她们一个已经上班,一个还在读书。三阿姨带我去过她单位,一样是好远,远到附近竟然有个养牛场,能看见大活牛。三阿姨管仓库,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摆着几张办公桌,一排排架子上放着各种东西,一道木栅栏的推门分隔内外。
我挺喜欢去三阿姨的单位,虽然她忙着上班,也没人跟我玩,但那里其实有不少好玩的东西。比如木栅栏的门猛蹬一脚站上去,可以来来回回晃半天。盒子里的回形针一个个穿起来,戴在手上、脚上、脖子上、头发上、耳朵上,亮闪闪的挺好看。食堂的饭菜简单可口,青菜加荷包蛋,尤其是荷包蛋,筷子一戳,橘红色的蛋黄慢慢流出来,拌饭别有风味。我在她工作的地方大闹天宫,她同事总要吓唬我说“你再皮,领导要来骂你阿姨了”。我就冲他做鬼脸,会么会么,像我这样好看又可爱的孩子(原来我打小自恋)。
在外婆家,小阿姨的手绝对是最巧的。结个绒线、钩顶帽子、织双鞋子,全是小case。她能看着书自己剪裁做衣服,有时候还能设计出新款式,什么裤子裙子睡衣罩衫,反正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搞定。她还会梳各种发式。我读初中那会儿,流行一种“百结辫”,好看但费工夫。我妈怎么都不会,她瞧两眼就明白。我于是周末到外婆家让她帮我编好,回去小心翼翼地睡觉,这样可以在学校美上两天。可她有时候不肯让着我,有时候还打我,我便叫她“胖头鱼”(她那时长得有点胖,也不知道谁给她起的绰号)。她正是爱臭美的年纪,最忌讳别人说她胖,又追着打我。我跑到外婆面前告状,外婆虽然说她,也不能拿她怎样,因为除了舅舅,她是外婆最宠的小女儿。

三
外婆有五个儿女,我妈是老大,大阿姨是老二,表妹是大阿姨的大女儿,比我小一岁,自云南出生不久便抱来上海,养在外婆家。我去外婆家主要和她玩,虽然有时不免吵架,但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干各种不靠谱的事还是我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一起看《青春的火焰》,在打烂了几个充气塑料球后,只能团了报纸在那里练“晴空霹雳”和“流星赶月”。一次,我不知从哪里拾来株枯枝,我俩在屋外的园子里挖坑种植浇水,想象着它有一天能吐出绿芽,开出鲜花。其实许多努力不过白费,有时也明明知道会是白费,却依然享受那执着的过程。自然我们也没少去上外印刷厂的废纸堆“淘宝”,捡一堆垃圾(各种被印坏丢弃的纸)回来。不过有一次我捡了本高等学校教材《古代诗文选》,虽然书已破烂残缺,却至今摆放在我的书架上,偶尔也会去翻翻。要知道《西洲曲》和《春江花月夜》,我都是从这书中背会的呢。
电视里只要放《茜茜公主》,我俩就一定要看,不管放几遍,不管多晚放,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半夜还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只有外公陪着我们(因为他要负责关电视和电源,哈哈哈)。
外公在外婆家是绝对的权威,舅舅、阿姨和我妈都怕他,我们却不怕,常常同他开玩笑,他也不会拿我们怎么样。有一次我和表妹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声念着挂在墙头镜框里的字,那是他和外婆退休的奖状。外婆退休后还在上外食堂上班,外公则整日悠闲。“某某某同志光荣退休”,
我和表妹念外婆的名字。彼时语文课正教近义词与反义词,“光荣”的反义词是什么来着……“某某某同志啥啥退休”,我们想起那个词,大声念着笑倒在床上。
外公身体健朗时,曾经带我和表妹去看电影。哪个电影院记不清了,反正离家有点远,要乘车。看的是啥倒还有印象——《岳家小将》,里面有首什么“小百合花”的歌,一直唱,一直唱。
那是个夏天,电影散场下起了雷阵雨,雨点砸在地上噼里啪啦。外公只带了一把伞,要遮住三个人有点勉强。外公撑着伞,叫我和表妹一左一右靠紧他,眼睛看着些脚下,别踩到水塘里。
可我们似乎总爱同他对着干,故意往伞外面挪。天气那么热,淋点雨正凉快,穿着塑料鞋,脚早湿了,还怕沾水?看见不远处有个水塘,走近了大步迈去,一脚踏得浪花四溅,开心极了。外公就这样带着我们一路跌跌撞撞回到家,被外婆数落——怎么你身上没湿,两个孩子都湿透了,伞都给自己撑了?嗯嗯,就是就是。我们一边偷笑,一边点头附和。
如果说寒假去外婆家可以享受过年的热闹与快乐,暑假可真是悠闲绵长的时光。每天洗了澡,吃好晚饭,点上蚊香,拿把凳子、搭张躺椅在院子里乘凉,听知了鸣唱,看星辰闪烁。
夜深了,乘凉的人一个个回屋睡觉,“夜游神”的我却睡意全无,外公也不睡,打着蒲扇陪我继续遥望星空。很多很多闪亮的星星,大小不一,缀在深蓝的天幕。有大大的一颗特别明亮接近于金黄的颜色,也有几颗小小的暗淡惨白,交错夹杂。
不知哪儿吹来了风,夏夜里难得的凉爽,知了不再鸣叫,可能也已睡着。我问外公哪颗是北极星,他指给我看北斗七星,偶尔竟有流星滑过。我又问他“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位置,他指了两颗出来,也不知道是不是瞎指。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他们家本来不姓“王”的。
我一下来了兴趣,问他不姓王姓啥,为什么会姓王?他说他们祖上是个什么王爷,太平天国时为了避乱而改姓,改什么好呢,思来想去,就改王爷的“王”吧,这些当地县志可是有记载的。
真奇怪,居然外公和我妈、舅舅、阿姨的姓氏是这么来的。那王爷原本姓什么来着?爱新觉罗、叶赫那拉……是满族的王爷还是汉族的王爷?是清朝的王爷还是太平天国的王爷?
那时候我或许太小,小到连这些问题都没有好好想,好好问。但长大了又怎么样呢,我还是没记得问。又比如都说外公的毛笔字写得好,我却从没跟他好好学过。我只是越长越大,去外婆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四
我刚工作没几年的时候,常在外面读培训班,学这学那,有时一读就要读一整天。
一天下午,课才上了一会儿,妈妈打电话来说外公不大好,叫我下课去趟医院。在这之前的十几年里,外公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年前他感觉有些不舒服,但我们都不认为会有什么大问题。
我继续听课,心里却不安定起来,也不晓得老师在前面说了些什么。课间休息,我决然拿着包离开。走到外面打的,市中心很难叫车,旁边正好是地铁站,我就去坐地铁。
我坐在晃荡的车厢里,心也跟着晃荡。我想自己一个学中文的,去读什么托福、GRE,是有什么毛病?电话又来了,是我爸打来的,地铁开门关门报站的声音有些吵,我听他好像说外公不行了,我大概赶不上了。
我拿着手机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说:“不要,等我!”
我挂了手机,站在车厢门前,等门再次打开,拔腿就往外跑。
这是哪一站,我不知道,我从没在这里下来过。我跑出地铁站,立在一条不认识的小马路上张望。正好有辆出租车开过来,我一扬手坐上去。我让司机快点开,我说我外公在医院。他开得很快,但我还是不停地叫他快点开。他报了个数字,说“小姑娘,不能再快了,再快要飞起来了”,我想飞起来就飞起来吧。
车子停在医院门口,我付了钱急急忙忙下车,连找头都没要。我奔进医院,奔进大楼,奔进过道,奔上楼梯。这个医院有没有电梯,不知道,反正我之前也没看见。病房在几楼?四楼还是五楼?我在楼梯上奔跑,飞快地转了一个又一个弯。
等我踏进病房,大阿姨第一个来扶我,大概我脸色很难看,又喘得不行。幸好她回来过年,幸好她过完年没马上回去。所有人都到齐了吧,外公还有呼吸。
但他没有睁眼,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医生说外公走了。
时间好像是下午三点三十三分,那天又是三号,好多个“三”,是要“散”的寓意吗?这是我第一次直面亲人离去,说不出的感觉。我和表妹木然站在一边,看大人们给外公换好衣服,送他去医院的太平间。
大阿姨在太平间门口摔碎了一只碗,我不懂这是什么仪式,但那个声音却清晰得叫人不能忘记。
爸妈要留在外婆家办外公的后事,我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他们叫我先回去。
小表妹(大阿姨的小女儿)那时的单位离我家近,她便跟着我回去,两个人有个伴。
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床上说了好多话,直到慢慢睡着。半夜里,我醒过来,发现台灯没关,昏黄的光芒亮亮照在头顶。我忽然觉得心里很难过,终归是有什么东西回不去了。

五
外婆家的门前也有座桥。
夏天的傍晚,外公打着蒲扇走到桥上纳凉,我和表妹有时会在桥上玩。那条河不宽不窄,离桥很近的地方有一根粗粗的圆管,凌空架在河面。我那时总有一种想站上去的冲动,想从河的这头走到那头。但我一次也没付诸实施,因为我虽然贪玩,却不敢冒险,实在是个谨小慎微的孩子。
我只是常站在桥上张望,看河滩的杂草在风里摇曳,看外婆有没有下班,看舅舅和阿姨有没有回来,看我妈有没有出现在路口。
那样的星空也只有那时才有,或许仍是有的,是我没有抬头仔细去看。
很少有人知道我其实是个爱热闹的人,我想回到那个自己还没长大、舅舅和阿姨都在一起的时候。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原文刊于《静·安》2024年春季号
(2024.VOL.10)
作者简介

乐茵,高中教师,静安区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静安民革《传承》编委会编委,静安区台联会理事。有小说、散文、诗词发表于《静·安》《联合时报》《上海民革》,获第六届中国当代散文精选300篇大赛一等奖,出版诗词随笔集《何物浓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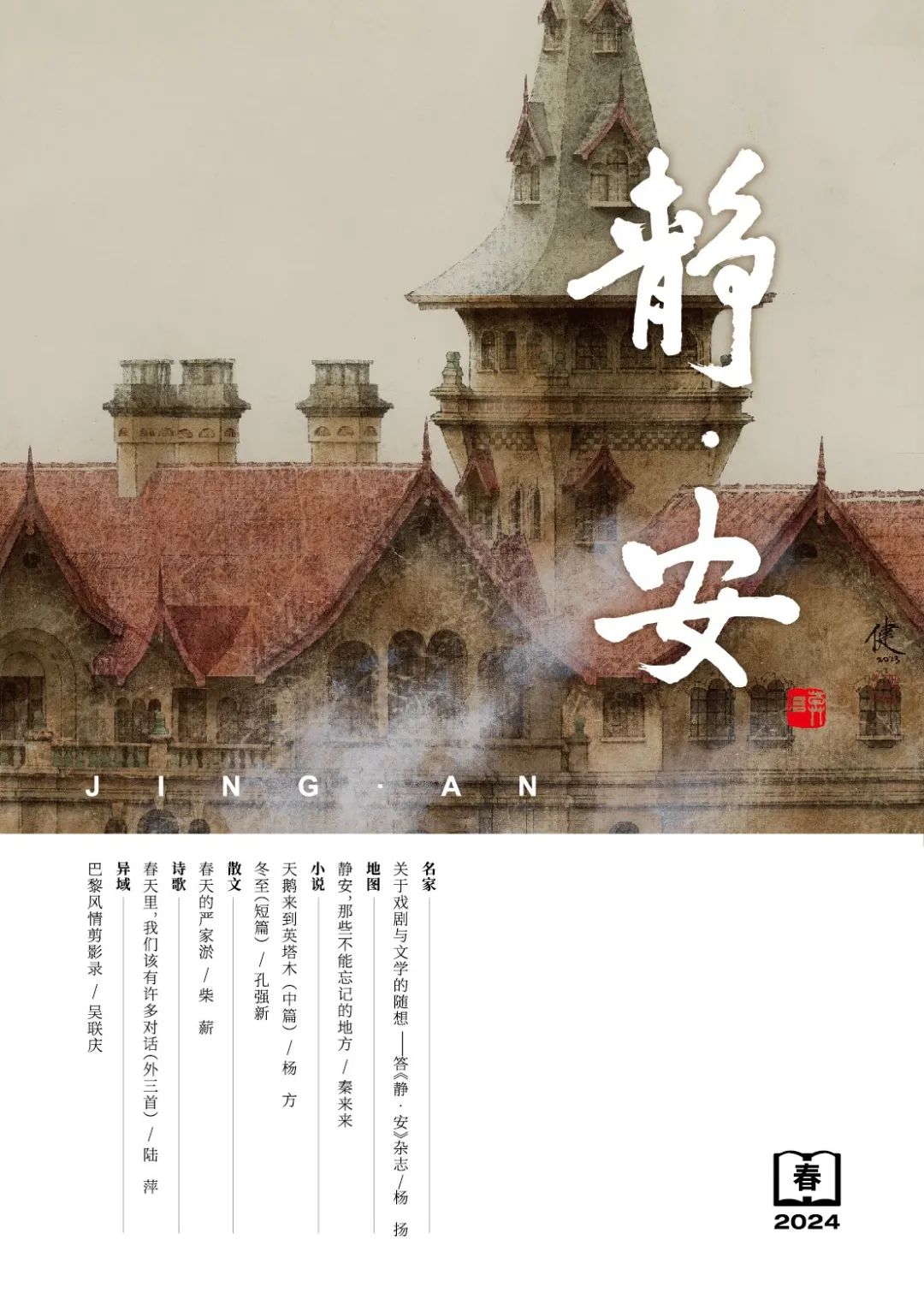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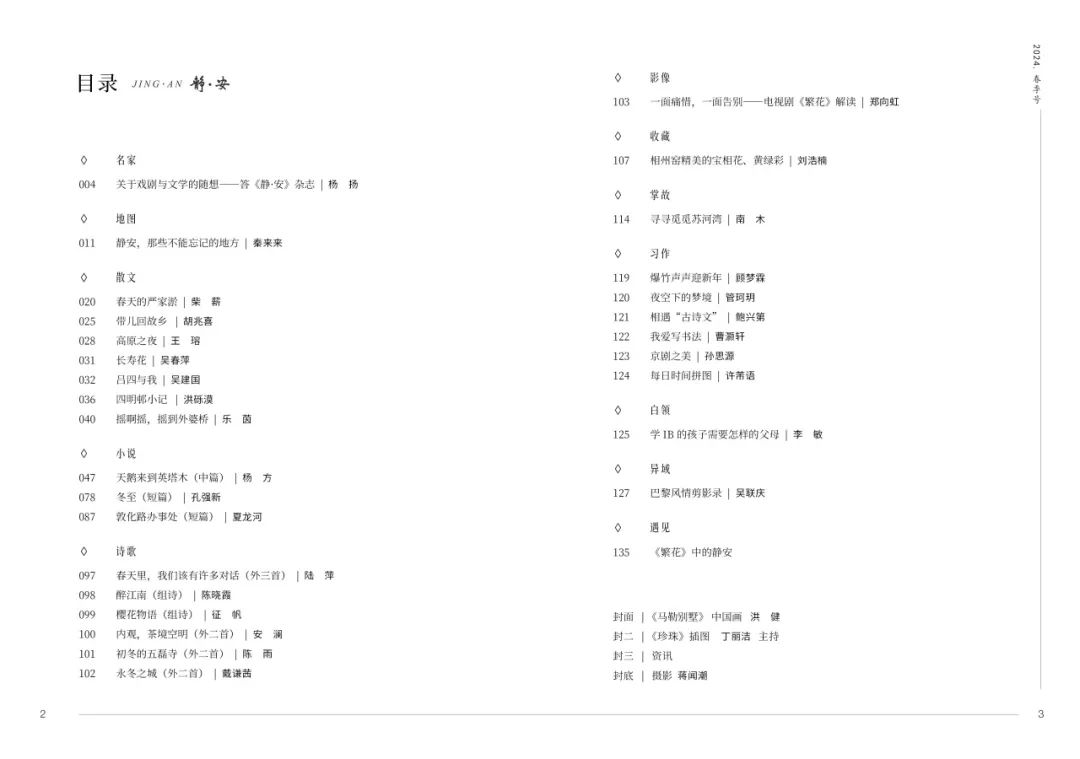

扫码关注我们
静安区作家协会
微信号|jaqzjxh
投稿邮箱jaqzjx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