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创刊于2021年,季刊。静安区作家协会和静安区图书馆联合主办,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题写刊名。既有名家之作、经典回顾,也刊登会员的优秀作品,旨在将文学情怀与静安的城市抒写相结合,彰显静安更具鲜明个性的文化软实力。
静 安
汪曾祺与上海
——《静·安》杂志访谈评论家郜元宝
《静·安》:郜教授好!你在2017年4期《扬子江评论》发表《汪曾祺结缘上海小史》,2017年5期《小说选刊》发表《一篇被忽视的杰作——谈汪曾祺的<星期天>》,2017年6期《文学评论》发表《上海令高邮疯狂——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2017年12期《文艺争鸣》发表《汪曾祺写沪语》。今年《文艺争鸣》4期又发表《汪曾祺留给上海的一张文学地图》,紧接着5月在《新民晚报》“夜光杯”陆续刊登“汪曾祺在上海”系列文章,目前已刊登到“之九”。
算起来前后差不多八年,你的汪曾祺研究似乎一直有意识地聚焦汪曾祺与上海这个话题。
过去也有不少人谈论过汪曾祺在上海的教书与创作,但像你这样锲而不舍、力求全面系统地分析汪曾祺作品的上海元素,探寻他在上海的生活轨迹,至少目前还并不多见。你为何对“汪曾祺与上海”或“汪曾祺在上海”这个文学地理学的课题如此感兴趣?
郜元宝:谢谢你,一下子收集到我这么多谈汪曾祺与上海的文章!
要问我为何对“汪曾祺与上海”或“汪曾祺在上海”这么感兴趣,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我研究汪曾祺,自己又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汪曾祺又确实与上海因缘不浅,这几个元素凑合起来,似乎我就不得不研究“汪曾祺与上海”之类的课题了!
当然还有更深的原因。首先我们理解一个作家,一种文学史现象,总离不开历史的时间与历史的环境,其中环境因素主要就是指特定历史时间的某个“地方”。“文学与地方”总是难解难分。不从某个具体的“地方”出发,简直难以深入地把握某些文学史现象。汪曾祺与“地方”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但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他生活时间更长的那些地方,比如故乡高邮,“第二故乡”昆明,晚年长期居住和工作的北京,包括下放地张家口。只有上海谈得最少。既然如此,那我就来谈谈“汪曾祺与上海”或“汪曾祺在上海”吧。
其次,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上海社会与上海文坛也值得继续耕耘下去。这是一个步履仓促而又内涵极其丰富的历史瞬间。虽然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如钱理群、陈青生等前辈)不断发表和出版了研究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文学的学术论著,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谈清楚。能否从汪曾祺这个小小的“点”介入,继续研讨40年代后半期上海乃至中国文学?我对这个假设充满着期待。
大概在2005—2007年之间吧,我经常去拜访李子云先生。我们往往一谈就是一下午。有时还会接着谈到晚饭的桌子上。话题之一就是40年代。这对于她是亲历过的历史,对于我则仅仅是依靠纸上遗迹来加以想象和建构的历史。两种历史观肯定难以沟通。但恰恰因为难以沟通,反而激起我们许多对话交流的兴趣。我现在终于可以沉下心来,对40年代后期的上海文学做一点小小的探索,这也算是我个人对李子云先生的一种缅怀吧。
《静·安》: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汪曾祺在上海私立致远中学教书,汪曾祺以此段上海生活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只有《星期天》。《星期天》是怎样一篇小说?为什么说它是“被忽视”的?在上海一年零七个月的生活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郜元宝:《星期天》是1983年夏汪曾祺在北京寓中“挥汗”创作的,发表于《上海文学》1983年10期。这是汪曾祺回忆他1940年代后期上海生活的唯一完整的作品。上海读者倘若对汪曾祺感兴趣,不可不读《星期天》。
这也是一篇构思独特、才华横溢的小说。有人说汪曾祺1970年代末“复出”之后,越来越走向传统,越来越回归高邮故土,越来越远离他40年代一度倾心的现代派文学。但至少《星期天》是个例外。《星期天》几乎绝无“高邮故里小说”那股子乡土气息,乃是纯粹的“现代都市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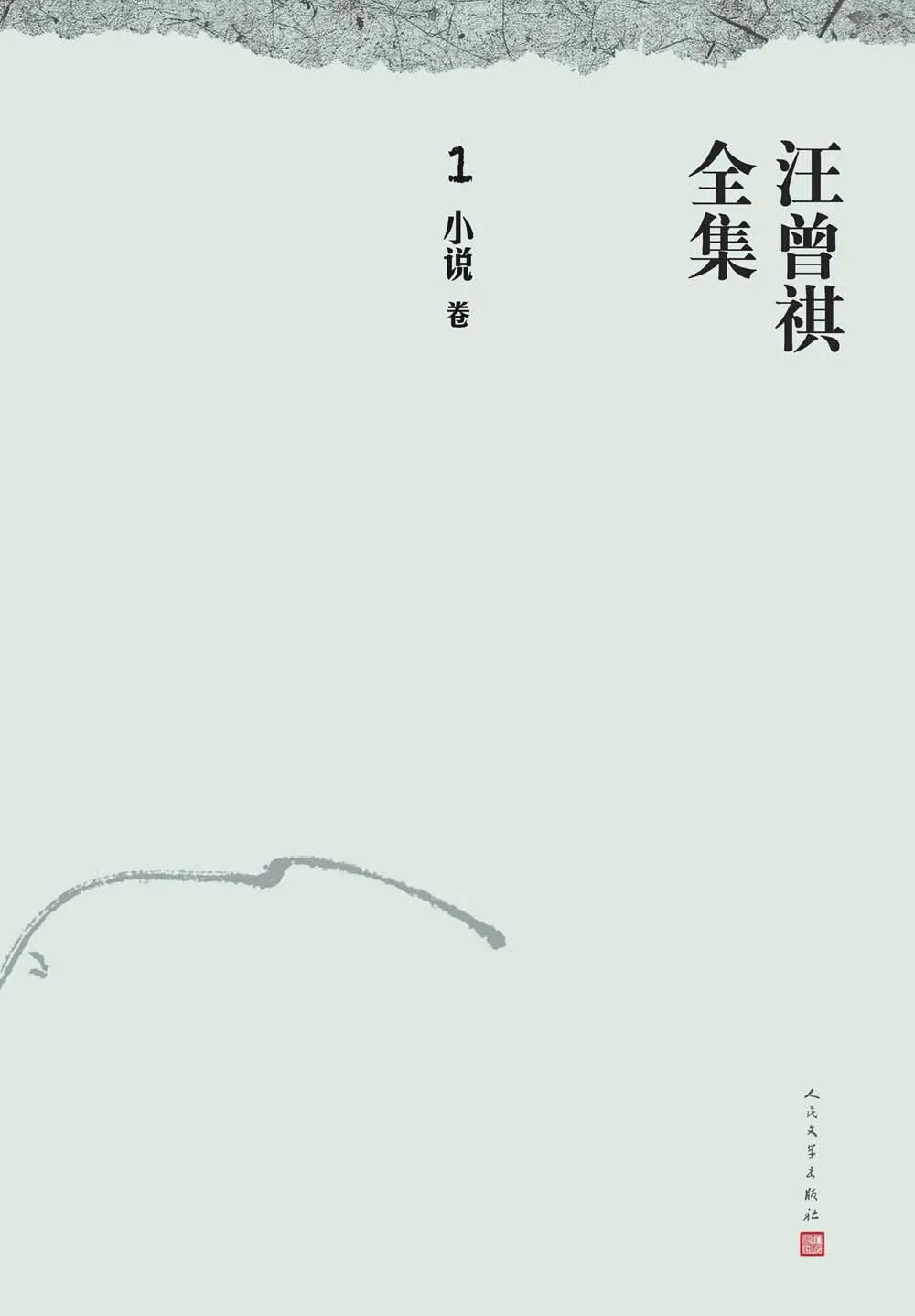
当然《星期天》也充满了传统文化气息,但其中也不乏汪曾祺年轻时一度沉湎(或者用他当时的说法叫“沉酣”)的现代派文学的风神,这既包括最直观的语言要素,也包括篇中自然流泻的对于人物心理类似意识流式的呈现,还有叙述者在整个叙述过程中自由说话的那种特别的精气神。
《星期天》发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受重视。一知名作家甚至纳闷:“汪老怎么可以这样写小说?”这主要指《星期天》写作上的另一个大胆而明显的特点:汪曾祺居然一上来就按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顺序,挨个儿介绍小说人物,然后才借助一场星期天的舞会,将这些看似孤立的人物集中起来,造成一定的情节冲突,并在最后的故事高潮中戛然而止。其实这种写法,汪曾祺可说是蓄谋已久。他很早就在跟黄裳的通信中说,不妨做类似这样的试验。这样写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不想多说,读者认真阅读就是。一句话,不仅我个人很喜欢《星期天》,由于一些有心人和热心人(包括在下)不停地奔走相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读者重视和喜爱这部作品了。
当然对研究者来说,《星期天》还是难得的探寻汪曾祺那时候在上海生活的“材料”。很奇怪不是?高产的散文家汪曾祺竟然很少完整细致地讲述他这段时间的上海生活,却愿意在虚构小说里集中地抖出一些“材料”。他为何要这样做?我真是闹不明白。这“老头儿”,鬼得很。
《静·安》:“汪曾祺在上海的步履间,藏着一代文人以笔墨勾连的文学地图。”其中巴金、萧珊的家是汪曾祺在沪期间走动最勤的去处。郑振铎、李健吾、唐湜、黄永玉、黄裳、施蛰存、叶圣陶、凤子、茅盾、郭沫若、臧克家、范泉、陈敬容、阿湛、单复、韦芜、萧乾、刘北汜、唐弢、柯灵……这些作家和编辑家彼此的交友印记,似乎都与汪曾祺有关。你以细节的考证,力求还原1940年代后半期天地玄黄之际大小作家之间的交际网络。记录时的感想怎样?做学问的功夫是否就在“一个也不漏掉”?上海期间汪曾祺发表过哪些重要的小说?“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沈从文1941年2月3日致施蛰存的信中语,基于对其学生怎样的认识?
郜元宝: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时,汪曾祺已经在西南联大崭露头角了。比如沈从文推荐发表在《国文月刊》上的《灯下》,就是后来《异禀》的第一稿,已经得到编辑《国文月刊》的西南联大老师们的推崇。
沈从文是作家,也是批评家,写过许多文学批评文章。他赞许汪曾祺,并非仅仅出于对自己弟子的偏爱。
汪曾祺在上海期间的作品,一部分编入《邂逅集》,1949年4月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还有许多作品当时散佚了。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汪曾祺全集》基本都已收集齐全。无名氏(卜乃夫)认为汪曾祺在上海时期最好的两篇小说,就是发表在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上的《绿猫》和《鸡鸭名家》。其实上海时期汪曾祺的佳作绝不止这两篇。《落魄》《戴车匠》《艺术家》《邂逅》《囚犯》等,都各有千秋。
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坛异常复杂。各个年龄段、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竞相登场。有的作品如钱锺书《围城》后来固然成了经典,但因为历史发展得太快,远比文学更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所以也有许多作家的作品被忽略过去了,无人喝彩。汪曾祺若非1970年代末“复出”而大器晚成,他40年代后半期在上海的文学活动也不太会像现在这样受人关注。
我只是觉得,现在再来看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在上海的创作,不能满足于就作品来论作品。最好能“重建”当时文坛和社会思想的实际状况,这样才能知人论世,更好地弥补文学史的这一段“空洞”。
这方面的工作我做得很少。许多优秀学者早就在做了,只不过对汪曾祺的上海时期的研究,至少目前还相对比较薄弱一点而已。相信很快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这个领域,贡献更好的研究成果。
我说我这方面做得少,绝非故作谦虚之态。我过去关注当代文学比较多,不大喜欢做现代文学方面的考据。但偶一为之,才发觉大有意趣,简直有点上瘾的感觉。说白了,还是做这样的工作难度不小。每一次,哪怕一点点证据的获得,一点点难关的突破,都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满足感。真的能做到“一个也不漏掉”吗?大概很难。
《静·安》:还想八卦一下:汪曾祺以及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怎样?沈从文寄来的稿费是汪曾祺在上海的重要生活来源吗?
郜元宝:目前暂无材料显示汪曾祺在致远中学每月取酬多少。1947年7月2日所作小说《绿猫》,写小说家“我”和另一个小说家“栢”(汪曾祺在上海时曾用过笔名“方栢臣”)都从云南来上海,又都很落魄,有一天“我”去拜访“栢”,见“栢”的房间有四张床,“比我的房间还多一张”,其狭窄、拥挤、凌乱简直不可名状,“我想问问他是不是还是那几个钱薪水,得了,别问了。”这也可以视为汪曾祺当时的自我写照。他的月薪肯定不会太高。他到了上海,也是诗人杜运燮笔下的一个“追物价的人”——否则他和穷画家黄永玉每次去见青年文友黄裳,不会总由黄裳会钞。黄裳担任《文汇报》编辑记者,又在“中兴轮船公司”兼职,笔头快,写散文赚稿费也多于汪曾祺、黄永玉。
学生眼里“汪先生”相当贫寒(那时上海人都称老师为“先生”),“有一次,上午第一节课是国文,过了几分钟,汪先生还没有来。班长便去宿舍里看看,回来的时候,对同学们说,汪先生还在睡着,感冒了,身上只盖了一床没有被里被面的棉絮。同学们听了,心情黯然。可见那时候的中学老师生活是多么清苦。”
小说《星期天》说赵宗浚校长每逢周末总忘不了把几个他乡作客或有家不归的单身教员拉出去玩玩,逛公园,坐茶馆,吃小吃,“凡有这种活动,多半都是由他花钱请客。在这种地方,他是一点也不小气吝啬的。”校长此举既是团队建设,也是聊补无米之炊,稍稍减少一点教员薪水不高的遗憾吧。
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提到黄永玉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说黄永玉的教师工资(低得)“不可想象”!他自己的工资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此稿费就很重要了。汪曾祺在上海时期的稿费分两块,一块是在上海本地发表文章的报酬,一块是在北方(主要是平津两地)报刊上发表作品的稿费。后者仍按老习惯,主要由沈从文帮他推荐,也由沈从文帮他将应得的稿费寄到上海。
《静·安》:你的《上海令高邮疯狂——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长文细致深入地解析了汪曾祺小说的上海元素。上海人形象在《星期天》以及上述“故里小说”中似乎都不佳,上海的现代摩登催折了高邮的传统文明。《岁寒三友》中一个人物“季匋民”有意无意地坑了同乡,就因为他的上海背景。而在《鉴赏家》中,隐去上海背景的季匋民就不再有十里洋场的投机与鄙俗,显出不俗的格调。上海味儿,于人物,于故事,在汪曾祺故里小说中常常是被嘲讽的对象。你说从1970年代末复出至1997年逝世,“汪曾祺着意经营的故里小说正面讲述了高邮古城的日常生活,也侧面涉及千里之外的上海。或者说,他描绘了时刻在上海阴影下败落和挣扎、清醒和疯狂的开放的高邮。远方的上海对高邮古城的影响是汪曾祺故里小说挥之不去的阴影。越到后来,阴影越加浓厚。这一点,使汪氏故里小说与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高晓声等同类作品相比,显得别有一种魅力。”以茅盾为例,他1916年来到上海,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交往的人比较上层,包括有从事银行工作的族亲,他了解的上海似乎更高位一些。这影响了茅盾后来的创作格局,如写作于1933年的长篇小说《子夜》。汪曾祺了解的多是小人物的生活,这种取材方式似乎也正符合他的风格,即站位很低,视角平视。如何理解汪曾祺自己所说,他的作品是“很悲哀”的,而“悲哀是美的”?
郜元宝:啊呀,这个话题我因为沉浸得太深,总觉得并非三言两语所可道尽,所以就允许我简单说一说吧。
我只想说,研究许多作家,局促于一地肯定不行。往往要做“跨地域”的研究。把高邮和上海结合起来研究汪曾祺,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学术试验。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从事这项研究。我敢担保,这种研究必有收获。因为作家的经历、视野、兴趣所在,往往就是跨地域的。也许有的作家一辈子未曾离开某处,但这是作者的肉身。作家的心灵不可能受限于某个狭小的地方。它一定是心游万仞、视通千里。这样才成其为作家。
汪曾祺对这个问题一直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确实说过,“我的小说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也就是说他善于用他的笔来留存记忆深处高邮古城那些令他感动的平凡人家所散发的“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但汪曾祺也说过,“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我的家乡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小城。因为离长江不远,自然也受了一些外来的影响。我小时看过清代不知是谁写的竹枝词,有一句‘游女拖裙俗渐南’,印象很深,但是‘渐南’而已,这里还保存着很多苏北的古风。”高邮不仅“保存着很多苏北的古风”,也因为“离长江不远,自然也受了一些外来的影响”。汪氏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想象空间,构建了完整立体且流动变化的高邮地方文化兴衰史。作者关怀被这种文化所化的雅俗高下各色人等的喜怒哀乐,试图揭示地方文化盛衰与人民哀乐背后轻易看不见的社会历史根源,亦即“外来的影响”与“苏北的古风”的此消彼长。
高邮传统文化在以上海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挤压下逐渐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写得愈真切,它所释放的凄艳之美就愈发感人。
《静·安》:你在2009年5月写的长文《汪曾祺的两个年代及其他》中,详细论述了汪曾祺的文学人生,他的坎坷岁月。你是否很敬仰汪曾祺的为人与性格?如果不热爱,是不能花费那么多心力去做历史考证的。该文两次提道:“汪曾祺这样的小说家以后还会出现吗?”——很难吧?
郜元宝:一般总以为你研究某作家,必定喜欢某作家无疑,甚至还会崇拜、迷恋。其实未必。我对自己研究的任何一个作家固然有喜爱敬重的一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慢慢保持一段距离,力图加以理性的审视。对汪曾祺就是如此。或许“敬仰”有之,却谈不上“热爱”。我也不是什么“汪迷”。
我这样说,可能令你感到意外。其实我倒觉得,这种对待自己所研究的作家的态度,才更加“平淡而近于自然”。
历史真是奇妙。有时候我们觉得时间凝固了,甚至发生倒流。不是经常有人谈论“历史上惊人相似的一幕”之类的话题吗?但你要说,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杰出作家,谁跟谁很像,我总觉得缺乏根据。汪曾祺就说他其实不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作家都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才华的本质和个性。很难复制。或许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吧?
我不记得写那篇文章时,为何两次咕哝着:“汪曾祺这样的小说家以后还会出现吗?”但我的意思,应该不是希望过些时候再出现一个汪曾祺。这不符合文学史发展的规律。
《静·安》:汪曾祺有许多写美食的名篇。如今写美食的当代大小作家也有很多。简直趋之若鹜。汪曾祺的写吃,与他们的写吃,有什么不同?汪曾祺这个美食家的理念与如今那些食不厌精的美食家又有什么区别?
郜元宝:我在《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5期发过一篇论文《与“恶食者”游——汪曾祺小说怎样写“吃”》,我认为散文家汪曾祺固然爱谈美食,但小说家汪曾祺却写了许多“恶食者”——也就是上海话所谓“吃相难看”的人。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美食家在生活中难免要“与‘恶食者’游”,难免要遇到各式各样的“恶食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想,写这些“恶食者”也是美食家汪曾祺的一项任务。他要告诉读者,美食家不等于懂得吃各种美食而已,更重要的还是如何优美优雅地去吃。要吃出风度,吃出人类对于食物应有的珍惜、尊重、敬畏和赞美。
可惜注意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美食家汪曾祺如何如何。比如小说《八千岁》那个富到开米行的“八千岁”,日常只吃最便宜的“草炉饼子”,或者“饭陪”(请贵客喝酒,自己吃饭作陪)。但他自己吃得很香,这算不算“美食家”?相反依靠地方武装鱼肉乡里、绑架勒索“八千岁”的那个“八舅太爷”,用勒索得来的钱铺张浪费,胡吃海喝,搞什么“满汉全席”,难道这样的人也算是“美食家”?“美食家”云云,掩盖了多少值得重视、值得反省的人与事啊。
《静·安》:汪曾祺对中国各地方言可谓兼收并蓄。沪语在汪曾祺作品中有着怎样的运用?你的评价如何?
郜元宝:我写过一篇长文《汪曾祺写沪语》。我发现汪曾祺确实爱“卖弄”他的沪语,不管有无必要,三不知总会来那么几句。专门写上海的《星期天》使用上海话最多,其他与上海关系不大的小说、散文乃至文论中散见的上海话也不可小觑。
他为何对上海话如此情有独钟?除了40年代后期在上海住过一年零七个月,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我在那篇文章中做了几点推测。比如他最好的朋友、西南联大同学朱德熙(语言学家、曾任北大副校长)是上海人,两人日常交往和通信都爱说(写)沪语。汪曾祺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沙家浜》期间,来过上海多次,跟上海沪剧团可谓紧密合作,等等。
但有一点还值得补充,即采用上海话乃是许多现代作家共同的“爱好”。上海在上世纪三40年代是新文学中心,许多作家要么在上海居住,要么路过上海,要么作品在上海发表和出版。总之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在作品中写一点上海话。鲁迅就不用说了。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那么不喜欢“海派”,居然也会在作品中偶尔写两句沪语。比如沈从文发表于1935年7月1日出版的傅东华、郑振铎编辑的上海大型文学刊物《文学》五卷一号的短篇小说《顾问官》,就让主角“顾问官”冷不丁来一句“胖大头军法长瞒我,那猪头三(学上海人口气)刚才还……”沈从文自己在上海住过多年,熟悉上海,但须知“顾问官”“军法长”之流皆地地道道“湘军”人物也。即使“顾问官”日常爱看《申报》,知道“猪头三”字面上的意思,但他岂能“学上海人口气”讲出“猪头三”三个字?
我觉得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作者沈从文本人熟悉上海。他又考虑到这篇小说要在上海的杂志上发表,因此即便与小说人物的身份不完全吻合,也不妨碍他偶尔用用上海话。汪曾祺爱写沪语,应该也是受到现代文学这个传统的影响吧。
(原文刊于《静·安》2025年秋季号)
作者简介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中国鲁迅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上海作协副主席。先后获得“冯牧文学奖”“唐弢文学奖”“王瑶学术奖”“鲁迅文学奖”等。著有《拯救大地》《遗珠偶拾》《时文琐谈》《小说说小》《汉语别史》《鲁迅六讲》《不如忘破绽》等。

扫码关注我们
静安区作家协会
微信号|jaqzjxh
投稿邮箱:jaqzjxh@126.com
《静·安》新媒体编辑部
主编:殷健灵
执行主编:崖丽娟
编辑:陈晨 李亚君 于洁